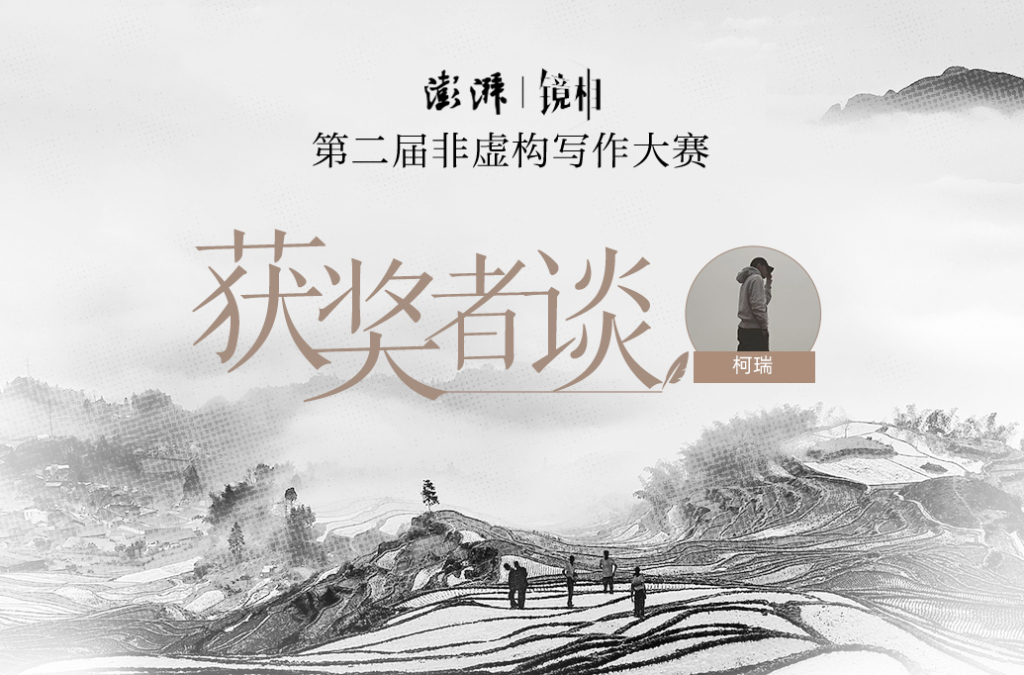
编者按:
近日,第二届“澎湃·镜相”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名单揭晓。本届大赛以“渺小与苍莽”为主题,旨在挖掘关照现实、书写时代与个体,记录磅礴与幽微的优秀佳作。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,七猫中文网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,上海作协担当指导单位,《收获》杂志担当文学指导,关注时代浮沉、家国命运、城市与乡村、女性叙事、真实罪案等众多题材,倡导以诚实的书写,展现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貌,理解自我与他者。
作品《加油站纪事》(点击链接阅读作品节选)聚焦于加油站从业者——“油K”群体,通过丰富的采访和详实的资料,为读者呈现了加油站行业的发展历程和人物故事,以小见大,反映出社会特定群体的奋斗与无奈。作品信息挖掘深入,文本叙事流畅,结构清晰,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和可读性。
以下是作者柯瑞的发言内容精选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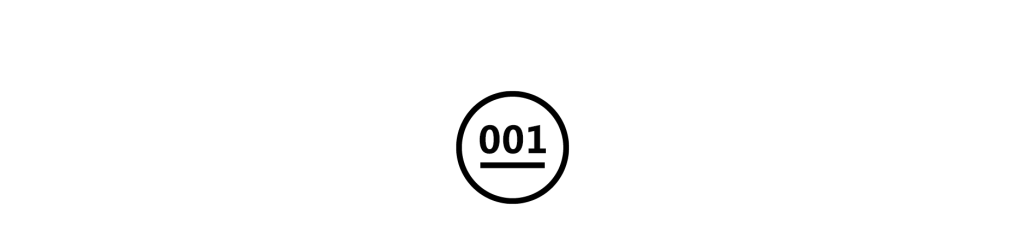
莆田人的淘金路
我一直把这种比赛当作抽奖,只是没想到自己会中奖。很惊喜,也很感谢主办方的认可。
这篇稿子的种子,是在一个很奇妙的时刻种下的。之前我在北京做记者,去年裸辞,变成“无业游民”后,为了防止生活脱轨得太严重,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作业,把老家加油站这个题当成自己的作业去写。
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加油站这个话题。它的背景是在福建莆田,一群来自莆田——通常是同乡、同镇或者同村的人——他们进入某个行业后,经过努力奋斗或投机取巧,逐渐把这个行业垄断了。
他们做的是民营加油站的生意。经过二三十年的打拼,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民营加油站是莆田人开的。所以你们以后再去加油的时候,会发现,除了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家之外,其他比如叫某某石油之类的,很大概率老板是莆田人。
加油站这个生意的逻辑其实就是一种农村商业化的非法集资活动。亲戚朋友因为信任你,大家出钱,比如你出1万、他出5万,把钱筹集起来,共同买下或租下一个加油站。带头的人通常会把全家都带到加油站居住,把生意做起来。中国在2009年成为汽车大国,加油站生意开始起飞,那时候做加油站特别赚钱。莆田人做加油站有一个特点:他们很看重宗族关系,如果你投了钱,他们真的会信守承诺,每年给你分红。
所以十年前,很多莆田人靠加油站致富。大家都知道这是赚钱的生意,所以只要有人毕业出来,很多人都会涌入这个行业。这有点像是一个平行世界:在城市的偏远角落有个加油站,住着一批莆田人,他们平时不跟城市的人打交道,只和自己的老乡往来,专注于赚钱,等到春节再回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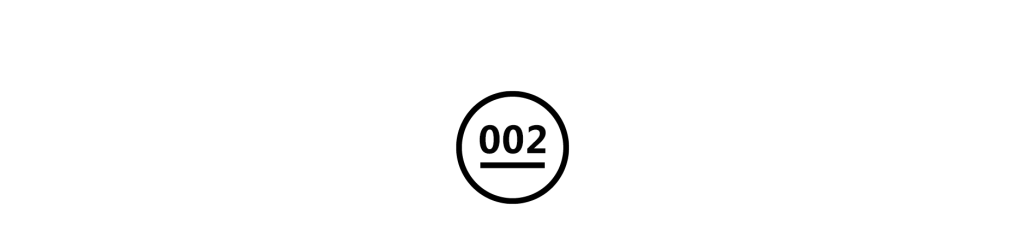
“我”与加油站的共鸣
生意的转折发生在疫情期间。现在,加上新能源车的冲击、税收政策的变化,加油站生意下滑很大。之前我以为加油站这件事体现了普遍重视宗族情谊,大家一起发财。但当行业遇到困难时,你会发现,伤害你最深的、坑你最狠的,往往是那些你很信任的亲戚。当这艘船要沉的时候,小股东往往是更先被踢下船的。所以这些年我听说了许多反目成仇的故事。
我想写这个选题时,首先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写:除了我是莆田人之外,我和这个题目的实际关联是什么。后来我发现有两点:之一,我本身对这种不确定性的生活状态很感兴趣。我有时候想,可能我们那边的人天生不爱上班,很多人都愿意去做生意,没有人觉得上班有前途,尤其上一代人都认为做生意才是好的。他们追求的是不确定生活,其实是我骨子里也渴望的。所以后来我在北京做记者也不坐班,辞职后就更不坐班了。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和他们共鸣的地方。
他们选择这个行业,就意味着选择了漂泊和动荡,选择了用巨大的不安全感,去博一个发财的可能性。这和我自己的状态很像,尤其是当我变成自由职业者以后,经常需要努力应对生活的变动。当然,他们想发财,我想的是写出好的稿子。前段时间我听李翊云的播客访谈,她说她自己是在无序的世界里,尽可能找到有序的生活状态,哪怕是一点点有序。我认为有序,其实就是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。
另一方面,现在这一代人——我身边的同龄人,不管去加油站做什么,都很难赚钱,最后都回来了,反而陷入更大的迷茫,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我感兴趣的是,当旧的世界秩序被打破,新的还未建立时,身处其中的年轻人会是什么状态。
对我来说,这个题还有一层私人的意义。那就是纪念我爸爸。他以前就是做加油站的,然而在要赚到钱之前,生病去世了,我希望可以把他留在文字里。
(编辑:吴筱慧;文字整理:苏怡菲)




